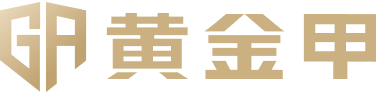暮色像浸了水的棉絮,沉沉压向黄公馆斑驳的墙垣。八十七岁的黄金荣蜷在雕花太师椅里,枯瘦的手指摩挲着楠木桌上的青瓷茶碗——那是当年杜月笙送来的寿礼,如今杯沿早已磨出温润的包浆,却再无人问津。窗棂漏进的风卷着梧桐叶打在玻璃上,发出细碎的声响,恍惚间,他竟听见年轻时自己踩着皮靴踏过石板路的回声,那声音曾震得整条华格臬路都发颤。

"黄老板,有人找。"管家李福的声音像块冰,砸碎了回忆。黄金荣抬起眼,看见个穿藏青布衫的青年站在门槛外,眉宇间带着股子狠劲,手里攥着的不是名片,而是把锃亮的匕首——刀刃映着昏黄的灯,泛着冷光。
"你是谁?"黄金荣喉咙发紧,手指无意识地抠进椅扶手里。青年没答话,反手将匕首插进桌案,木屑纷飞:"三年前,我爹死在你手里。那天他在十六铺码头扛货,你手下说'碰坏了金爷的货就得赔命',可他哪有钱?最后被人按进黄浦江,连尸骨都没捞着。"
黄金荣瞳孔骤缩。他想起来了——那年确实有个叫阿根的码头工人,因为碰碎了一箱洋酒,被自己的门徒拖去喂了江鱼。当时他还夸那小子"办事利索",如今想来,那笑声像钝刀子割肉,疼得他太阳穴突突跳。
"你要干什么?"他强撑着威严,声音却抖得像风中的落叶。
青年逼近一步,匕首尖抵在他心口:"今天,我要让你给我爹磕头。"
黄公馆的空气凝成了块铁,压得黄金荣喘不过气。他望着青年眼底燃烧的恨意,忽然想起自己十九岁刚混迹江湖时,也是这样眼神——那时他为抢地盘,亲手打断过竞争对手的腿;为讨好洋人,把同胞往火坑里推。如今报应来了,却是以这般屈辱的方式。
"我……老了,经不起折腾。"他试着妥协,喉结滚动着挤出几个字。
青年冷笑:"你当年杀人的时候,可想过别人经不经得起?"匕首又往前递了半寸,刺破了他胸前的绸衫,渗出血珠。
黄金荣闭上眼,往事如潮水般涌来:他从一个街头小瘪三爬到"上海皇帝",靠的是心黑手辣;杜月笙称他"大哥",张啸林给他递烟,可那些风光背后,是多少人家的妻离子散。如今山河变色,解放军的炮声已在城郊响起,他昔日的势力早成了明日黄花,只剩这栋空房子陪着他等死。
"我跪。"他睁开眼,浑浊的眸子里浮起一层水光,"给你爹磕头,也给所有被我害过的人磕头。"
青年愣住了,匕首"当啷"一声掉在地上。黄金荣吃力地从椅子上挪下来,膝盖接触青砖的瞬间,他听见关节发出细微的脆响,像有什么东西彻底断了。他缓缓低下头,额头触到地面时,尘土沾满了鬓角的白发——那白发曾是他在赌场赢钱时的骄傲,如今却成了耻辱的注脚。
"我对不住你们啊……"他喃喃自语,声音轻得像耳语,却被寂静的厅堂放大了无数倍。青年站在原地,看着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佬在自己面前跪下,忽然觉得心里那团火慢慢熄灭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悲凉。
不知过了多久,黄金荣才重新抬起头,额头上留着一块青灰的印子。他望着窗外愈来愈浓的夜色,忽然笑了,那笑容里没有往日的跋扈,只有释然:"时代变了,我也该走了。"
当晚,黄金荣让人给青年备了盘缠,亲自送他出门。走到门口时,他停住脚步,指着门楣上褪色的"忠义"二字说:"这两个字,我配不上。"青年没说话,深深鞠了个躬,转身消失在弄堂深处。
第二天清晨,黄金荣换上了洗得发白的粗布衫,拿着扫帚清扫院子的落叶。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他佝偻的背上,那模样像个普通的老人,不再有"上海皇帝"的影子。或许他知道,这场跪拜不是终点,而是另一个开始——属于赎罪的,迟到的开始。
(全文约750字)